作家簡介

漢名趙聰義,1981年生,布農族,成長於花蓮卓溪鄉中平nakahila部落。曾經就讀於元智大學中文系,畢業於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目前在部落成立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做為田野工作的空間。文學創作曾獲得2000、2001、2011、2013、2015年原住民文學獎,2008、2011年花蓮縣文學獎,2011、2013年教育部族語文學獎。著有《笛娜的話》、《部落的燈火》《祖居地‧部落‧人》。
書評與訪談
Book Reviews and Interviews
頭帶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物品,每次上山都要跟笛娜借,深怕哪一天被我弄丟,於是抽空跟黃泰山學習製作頭帶,一個月的學習中,讓我擁有專屬的頭帶。出生在拉庫拉庫溪太魯那斯的Tina Umav,已經九十多歲,曾經跟我說過,以前藤編只有Isbabanaz這一個氏族才可以編,其他家族都要向他們以物易物,來換編織物,她如此說:
naitun maqansia matas-I balangan、tuban、sivazu、davaz、at talangqas、
kaupakaupa tindun qai Isbabanaz a tindun, maqa ata qai mabaliv ata,只有他們可以製作背簍、籐籩、網袋、 talangqas ,只有 Isbabanaz 氏族才可以做這些,其他氏族就向他們買。
──【觀看全文】
Salizan坦言,「大哥知道我想做文化記錄,減輕了我背負的重量,讓我可以記錄山林的故事。野外新手什麼都做不好也走得慢,但凡事跟著做,從找柴、認山頭學起。」同時,研讀清代、日治時期大分、喀西帕南事件至國民政府遷台等歷史材料,「空間」逐漸轉變成「有意義的事物」,再回到東部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則嘗試運用學術方法闡釋拉庫拉庫溪流域語言、權力、空間的命名。……
──【觀看全文】
活動名稱:朝向台灣「新文學」:新世代作家群像
演講題目:文獻與文學的結合–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的生活
時間:2019∕11∕01(五)13:20-16:1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台文所A309教室
記錄人:陳卉敏(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沙力浪老師的演講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談到自己的生命歷程與文學啟蒙,分享自己如何開始寫作、畢業後回到部落與從事山屋管理員的工作;第二部分談文獻與文學的結合,並以詩集《部落的燈火》為例;第三部分介紹自己新書中的架構、重要信息;會後有簡短的提問座談。

沙力浪老師與主持人王惠珍老師
一、文學的啟蒙與延續
出身布農族的沙力浪老師說自己在國高中時期就開始創作,一開始專注於個人的心情書寫,後來有老師建議他試著將自己的文學轉換成族語,後來他就專門寫和自己族群有關的故事。大學時沙力浪老師就讀元智中文系,大一時參加了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以〈笛娜的話〉得到詩歌組佳作,自此他也對創作更有信心,繼續往下開展自己的寫作生涯。不過在創作以外的時間,就讀中文系的他必須修讀聲韻學、訓詁學這類專精的中國古典文學知識,又要背誦唐詩,到了大二時也就慢慢產生困惑,他想:現在的漢人都不會用這些了,自己一個原住民學生學這些作什麼?加上班上只有他是原住民學生,茫然的心情也就更深。「在大學是一種尋找鹽巴的過程,自己好像失去原住民的味道。失去原住民的味道就像一盤菜沒有味道,失去鹽味。我想要找自己的影子、想要找一些像小米酒或糯米糕的味道。在大學的時間是失去鹽分中的歲月,然後在尋找鹽巴中度過。」他這麼形容當時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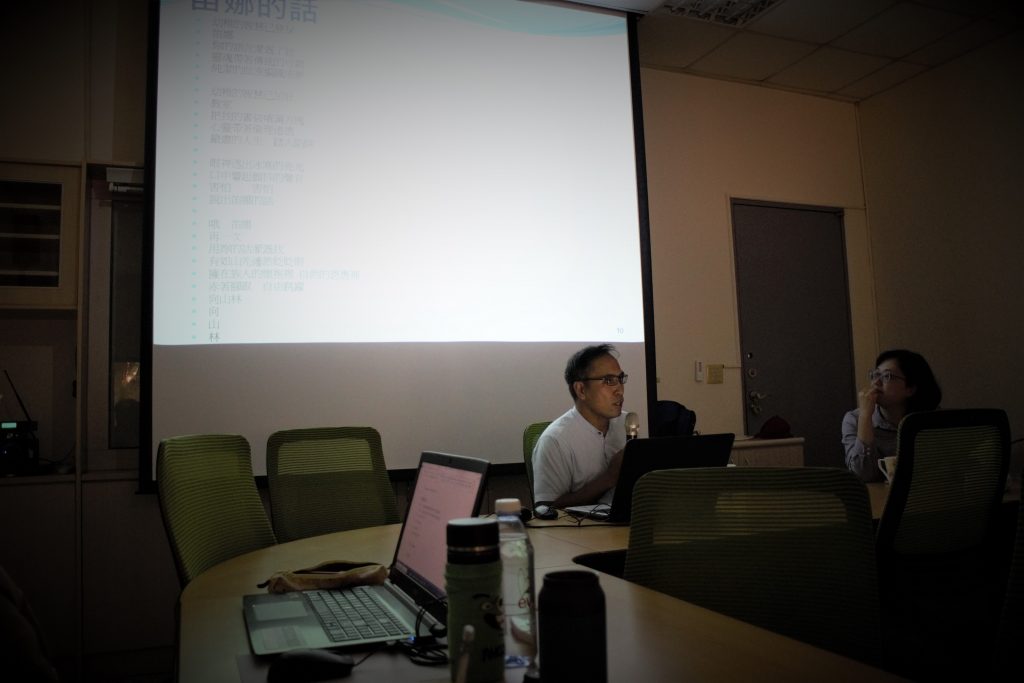
沙力浪分享〈笛娜的話〉
後來,系上有一位教授台灣史的老師鼓勵他:「你在中文系,可以把這些學問當成一個工具。把它學得很透徹,你就知道別人怎麼寫自己的生命經驗。看看李白怎麼去寫他的成長過程、寫自己的喝酒經驗等等,你把這些學起來、轉換成自己的東西,再去寫部落的事物。」他聽完以後覺得很有收穫,於是慢慢轉變自己的想法,開始認真書寫自己的東西。
畢業後念研究所時,他開始想要回到部落做一些事情,於是就近讀了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沒想到,本以為會有更多時間回部落,結果發現讀研究所卻是一種「和文獻、書籍對抗的生涯」,為課業繁忙之下,他幾乎沒有時間回部落。不過,他也在這樣的苦悶日子下寫出了〈我在圖書館找一本適合喝的酒〉。他發現賣場的每個紅酒瓶都像一本書,上面介紹了紅酒的歷史、酒精濃度,而自己背誦學術專有名詞也像在喝高濃度的酒,因為喝完的隔天會宿醉,然後問自己「怎麼唸了那麼重的書?」他說,在這段研究生活中,他一直想要「找到自己的小米酒」,因此不停在文獻當中尋找原住民的東西,最後卻發現這些「酒」的口味都來自於第三者,將原住民或浪漫化,或詭異化,都不是屬於原住民自己的小米酒。
這樣的想法一直延續到研究所畢業、退伍之後,他原本選擇到學校工作,可是過了一年,他還是心心念念著「那瓶小米酒」,於是又回到部落,在那裡建了一座小圖書館,專門擺放原住民相關的文獻。在經營一年之後,他發現這些文獻書籍無論作者身分是否為原住民,幾乎都使用漢語書寫,而自己既然回到部落與耆老一起生活,就乾脆成立一個獨立出版社,專門出版族語書籍。接著他開始在部落作田野調查,將老家的語言收錄在筆記本上預備出版。一開始部落的人不曉得他的理念,母親也以為坐在電腦前的他是「在北部失業以後整天看電視、不拔草工作」,直到他將部落的歷史喀西帕南事件寫成書,又做了族語辭典,並且在部落中為三位參與其中的耆老舉開一場新書發表會,大家才慢慢認識到他的工作。
後來,他為了有更多的資源為部落做事,便開啟了另一份工作:山屋管理員。這份工作被他形容為「三千兩百公尺上的民宿老闆」。在嘉明湖山屋裡,他最喜歡的部分是晚上的管理員課程,每當到了這個時段,除了宣導高山症、中暑的注意事項外,他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對山友講述布農族的故事。「像一般人都說嘉明湖是『天使的眼淚』,或是『藍眼睛』、『藍鑽石』,這其實是很西方的名字。我在那邊會講一個我們布農族產生出來的故事,叫做『月亮的鏡子』。」這份工作持續到現在已經四年,他說:「我希望把傳說和地景結合,因為一般人如果輕輕走過去,就會和在地的歷史擦肩而過。我在雲端上也會思考自己族群的歷史。每個命名都有布農族的智慧,我在三千公尺的雲端上,把祖先的智慧一一存到雲端。」

山區工作
二、文獻與文學的結合
談到研究所的生活,雖然有苦悶之處,但文獻的閱讀與書寫卻也讓他認識更多東西。比方說他的碩士論文〈拉庫拉庫溪流域語言、權力、空間的命名——從panitaz 到卓溪〉便以故鄉拉庫拉庫溪的歷史為題,而後續文學創作也經常從這個研究中獲取養分。他首先介紹過去以拉庫拉庫溪為題材的創作者,說明「文獻的支撐加強了真實性,讓小說彷彿歷史,令人想看下去。」接著他談到自己的創作詩集《部落的燈火》,以自己的創作為例說明。另外,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收集了許多族裡的故事,針對歷史與想像,他特別說明一件事:「每個傳說都像山上的霧,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而不一樣造成朦朧的美。不是誰說的不對,是每個人有他述說的方式、對歷史的詮釋。口述調查不一定要很精準,去查到底是哪一棵樹,洪水到底怎麼造成的。這些都有他的說法,因為這些的不同而成為朦朧美。」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來到大水庫,那時還是十九歲的大學生,跟著自己的大哥來到山上。本以為是普通的爬山,沒想到一走就是十四天,過程中幾乎沒有洗澡,進入山之後,他覺得自己一生中大概就去這一次:「因為就只是一座山,都是山,霧裡的山。對我來說就是跟著大哥進入山裡面。」後來到了第三天,他們兩人站在大水庫山中,大哥開始進行祭拜儀式。他問大哥「為什麼我們走了三天要祭拜?」大哥回應他:「因為這裡是我們的傳統領域」,接著開始介紹族群的歷史。而這一次的經驗讓他知道原來這些山不只是「霧裡的山」,是跟自己、跟父執輩關係密切的一座山,於是他這回進去之後就「出不來了」,每年都會再上去,碩士論文在這邊,文學書寫也在這邊。
「我開始認識到山不只是山,有歷史在裡面,進去裡面你才知道山的歷史。你可能從石頭可以知道山的年齡,從山的考古現場可以知道原來裡面不是只有我們布農族……會發現到三百年前,我們還沒進入到拉庫拉庫溪以前,已經有人進入到山裡面。這些都是透過進去山,或是很深入之後才會發現歷史。」想要認識這塊土地,而認識以後就進入到文學裡面。
談到創作〈翻山越嶺至馬西桑〉時,他特別指出許多人以為寫詩只是靠靈感,但是「靈感只是給你一個簡單的想法」,比方說他在這首詩當中的靈感是「把山圖像化」,不過如何「把這座山實踐出來」,仍然要從文獻中尋找材料放進去。「所以詩不單單只是靈感的展現,要怎麼把靈感留下來,靠的就是唸過的書、讀過的文獻。」
而另一首〈森丑之助的行腳中遇見阿拉〉,靈感來自他某次在文獻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沙力浪」。他解釋「阿拉(Ala)」代表部落中的同名者,由於布農族人命名採襲名制,每個人的名字都是承襲家族長輩的名字,所以有許多同名的情況產生,而同名者彼此互稱「阿拉」。「阿拉」之間會有特殊的情感聯繫,家族中同名的長輩通常會給和自己同名的晚輩多一份照顧,而異地中遇到同輩的「阿拉」,也會互相多喝一杯。而他在森丑之助的文獻上看到一個住太魯那斯的頭目是自己的「阿拉」,就讓自己化身為森丑之助的高山協作,跟著進去部落、山林,去探問當年的「蕃人樂園」是否實現,並帶到如今的原住民自治問題。整首詩示範了文學如何從靈感發生,藉由文獻的支撐完成。
三、新書簡介:《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
沙力浪老師解釋這本書是想用歷史的角度去看布農族人如何用頭帶背起一座一座山。頭帶是布農族重要的背負工具,他說:「布農族以前在清朝人、日本人還沒來以前,其實是用自己的身體去背石板、石頭、小米和獵物,然後建立自己的家園。清朝人、日本人來以後,其實我們的身體就被讓渡給政權,幫日本人蓋橋、蓋路,背他們的石頭、幫他們蓋駐在所。我們用頭帶讓渡自己的身體,去幫政權蓋出自己的家園。」因此書中的三篇〈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百年碑情〉、〈淚之路〉是以歷史角度為經,以自己踏訪的腳蹤為緯,從布農族的頭帶、高山協作與巡山員歷史談起,到日治時期遺留的八通關古道上幾座紀念碑的故事,最後以同心重建、修復布農族傳統石板屋的一段故事作結。從前在其他政權下是不得已讓渡自己的身體、為他人蓋家園,如今族人要回歸自己的身體,建造自己的房子。他引用孫大川老師的推薦序,說明原住民最重要的其實是歷史主體的重建和自己文化的重建,而這些不假他人之手,是自己族人要有共同的意識來參與、實踐。這是沙力浪老師回歸部落至今一直在做的事,未來也將繼續下去。
演講的最後,主持人王惠珍老師以日本白川鄉合掌屋為例,說明遺產不在於建築物,技藝本身就是重要的遺產,並期許布農族石板屋的技藝與部落的知識能傳承下來,成為世界的文化遺產。在會後的簡短座談中,有同學針對老師詩作的特殊「科技」主題提問,老師也以一首「用程式寫的詩」〈網路叢林〉答覆,並且在座談最後補充分享在建造石板屋時認知到布農族與排灣族石板屋的工法差異,以及技藝在世代傳承、文化保留時需要的取捨。整場演講活動圓滿結束,也帶給同學諸多收穫。

觀眾提問

大合照
來自於花蓮縣卓溪鄉中平部落布農族詩人與文學家,用心關懷部落,心繫族語與部落,決定回到家鄉用行動來連結傳統,一個練長跑的布農青年,是什麼動力與想法,把腳下的力量轉化成文字, 跳躍於字裡行間?本週就來聽聽他讀詩說故事吧。
──【聆聽廣播】
「我曾經經歷過流失母語的歲月,所以一直很希望能找回我的母語。」沙力浪表示,當他回到部落與不會說中文的母親對談時,發現小時候曾經流暢的族語竟然會結巴,甚至有時會無法理解母親說的話,對他而言,這是一種莫大的挫折與衝擊:「我怎麼會離媽媽的語言愈來愈遠呢?」
流失母語的衝擊,促使他回到部落從事族語保存工作,「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不同,很多族人因為工作的因素無法回部落,我因為讀書的科系及所了解的資源與知識較多,也有多餘的時間和能力可以貢獻在族語保存上,為什麼不回到部落協助族語紀錄與保留呢……
──【觀看全文】
